這是一篇關於《三牲獻藝》的音樂分析,但也論及臺灣本土文化神道、中國易經與當代電子音樂流行文化之間的互融關係。
《三牲獻藝》是一個落實風土採集,並將電子音樂與台灣廟宇音樂元素混種、融合的電子音樂跨界長程計劃,也是一個全新形態的電子音樂演出團體;由知名音樂製作人-柯智豪所發起,加上另位兩位音樂圈重量級電音製作人-鄭各均(Sonic Deadhorse)、黃凱宇(fish.the)所組成;並有年輕策展人賴士超、民俗顧問許泰英及 VJ(即時影像投影/演出)邱智群、落差草原 WWWW(立體裝置/主視覺形象製作)等所組成的藝術團隊-《天語公社》熱心參與製作。

在台灣近三百年廟會歷史中,藝閣上扮演過各式各樣的神話戲劇人物,藉此呈現民間傳說或小說戲曲之故事情節,不但在藝術展演於民間深根發揮力量,更有資訊傳達寓教意義。創作者將在原本代表著結束的儀式中,王船上的紙雕因為燃燒而混雜、拼貼在一塊,仿佛一隻新的混種神獸正在誕生,於是延續著《2013年混種現場-大演歌》的實驗精神,以陸/海/空三方神獸的姿態來形塑,「三牲獻藝」這名字就這樣誕生了。
延續這樣多元展現、敬拜天地的精神,創作者們將自己轉化成了獻藝的海、陸、空三種牲禮的角色來創作;當傳統文化在現今社會慢慢地流失,我們思考著如何將前人累積下來的美學聯結現今語彙,使更多人重新擁抱屬於我們的文化;同時亦從創作者的角色出發,透過跨領域合作激發新靈感與可能性。《三牲獻藝》更期許成為各世代聲響創作者找到數位聲響與傳統文化的橋樑,也提供傳統藝術一條重新回到當代生活中的一條道路。
 日本動畫電影《攻殼機動隊(Ghost in the shell innocence)》中對於臺灣宗教廟會的印象連結
日本動畫電影《攻殼機動隊(Ghost in the shell innocence)》中對於臺灣宗教廟會的印象連結
這是一篇遲來的《三牲獻藝》樂評。緣於三月下旬,我在臉書上看到轉錄的《三牲獻藝》宣傳影片與企畫文案,因為我本人有做過一個東西叫《易經紙牌》還在賣 ,便注意到了圖中文字「三牲」「獻藝」所配的卦象。當時我提到:
這部宣傳影片中,右邊「三牲」配的卦象是風雷「益」,「獻藝」配的是澤山「咸」。風(艮)倒過來是雷(震),澤(兌)倒過來是山(艮),製作者可能頗通易理,也可能只是在八卦裡選了這四個倒過來不一樣的卦象來配(因為乾、坤、坎、離倒過來都一樣)。然而,這兩卦的卦象與意義,也都很可以和這個企畫的精神交互發明。
十幾分鐘後我收到了私訊,居然就是三位作者之一的柯智豪先生發來的。原來是 Lydia Lu 看到了我的隨筆,告訴他說可以找我來寫個樂評。柯兄說:沒想到這麼快就有人發現我們埋的彩蛋。我們聊了一會,交流了一下關於傳統民俗信仰和現代電子音樂的想法,我聽了 Youtube 的版本說這個光在電腦上看不行,應該要聽現場,至少也得聽 CD,等到出片我一定買。然而到了發片日期,在各大唱片行苦尋不著均無進貨,後來託請柯先生寄了一片予我才有機會從頭到尾好好聽了幾遍。
您可以點擊下方圖片來試聽或購買本音樂
陸方-鄭各均/Sonic Deadhourse
「音速死馬」鄭各均的作品負責專輯的第四到六首:〈仙姬送子〉、〈頂下郊拚〉、〈荒煙古吹〉,專輯企畫案中說這三首使用了他招牌的「冷調、迷幻、碎拍」手法;我聽〈頂下郊拚〉還聽到了「斷片」,就是音樂有一下沒一下好像壞檔或者磁頭故障,我特地問智豪兄說這是故意做成這樣的,還是檔案有問題?答曰:故意的,沒錯。我聽完以後,說:「我只覺得,我好像聽到了來自異次元的音樂。」智豪兄答:「我們也這麼覺得。」
鄭各均不是故弄玄虛,他天然就是玄虛的,相對於我們來說。他連結傳統與當代,從古老的儀式萃取本質,轉化成新的形式,發人深省地回應了我們關心的什麼議題。鄭各均就是一個活在異次元的人,他大腦接收到的訊號,和我們普通人完全兩樣,而他做音樂給我們聽,就是告訴我們他感知到的世界是什麼樣子;他從廟會音樂取樣,改編重組給我們聽,也只是告訴我們他從這音樂聯想到了什麼,這一切都是直覺。
〈頂下郊拚〉指的是發生在 1853 年臺灣著名的械鬥事件,頂郊與下郊雖然都算泉州人,但也各擁鄉親和神明,而為爭地盤大打了一場。曲中各種斷片和刺耳的音效,大概就是小各跨越次元從一百六十多年前的現場接收到的訊號吧,我真覺得只能這樣講,再多講便是過度解讀。
〈荒煙古吹〉以廟會音樂開場,然後電音營造出一個荒涼迷幻的場景,接著出現了古琴曲〈梅花三弄〉──我很訝異,音速死馬怎麼會想到把這種最雅的文人音樂,和大俗(俗而大)的廟會音樂弄在一起?廟會不可能用古琴的,除了孔廟。而它又是以直覺的、私密感應的電子樂貫串起來,這便成了一個三角,妙!
這對立統一、正反合、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哲學,是我的思維而不一定是音速死馬的思維。我學過一點古琴,認得出〈梅花三弄〉,也知道前人賦予它的文化意蘊;但活在異次元的音速死馬,對這琴曲的感想會和我們傳統派一樣嗎?不管怎樣,〈荒煙古吹〉呈現出來的,就是很異樣。

〈梅花三弄〉的主旋律與廟會音樂相繼奏出,在荒涼的電音背景裡迴盪,就像似有還無的梅花重影,在顯界與靈界之間的境界飄零,承載著古人對更古之人的想像。這什麼意思?先別管什麼意思,這是他的感知。曲終處,突然就斷了,一個終止式都不給,這又是為什麼?不知道,可能單純就是因為這個異次元來客看夠了。
電音和「荒煙」的對應很明顯,〈梅花三弄〉和「古吹」呢?這琴曲是絃樂,而「吹」較接近管樂,這要怎麼解釋?《莊子‧齊物論》的「夫天籟者,吹萬不同」來索解:風吹過萬物,發出各種不同聲響,這叫天籟。古琴曲〈梅花三弄〉是對天籟與生物的一種感悟、提煉與再現,自然也可以說是「古吹」,何況這首曲子也是又一層的對古代世界的自然與人文的感悟、提煉與再現,故此,可以說鄭各均實現了傳統的翻新,真是可大可久、可喜可樂。
我問柯智豪兄,答案是小各認識一位古琴老師,常常合作應該有幾年了。而如果要我講我個人的觀感,那麼既然理論和知識在此無效,我也得回歸直覺才好。能讓我們聽到這個異次元鬼才是怎麼感知我們這個次元的,這就有天大的開眼界的意義與價值了,還不夠嗎?他的大腦一口氣把過去、現在、未來,民俗信仰、文人傳統、後現代電音,1和B和ㄇ通通攪到一起,組出一首他覺得聽起來應該會不錯的東西,給我們聽!找外星人不用去美國了,我們有土生土長的跨次元住民。至於你能從他的音樂裡聽出什麼,就看你頭腦裡本來的想法能否與它激盪一下。

海方-黃凱宇/fish.the
相形之下,「Fish」黃凱宇,和柯智豪兄的音樂,給我的感覺就是我們這個次元的,不故弄玄虛很好懂。Fish 擔綱的開場曲〈威鎮邪魔〉以鑼鼓開場,然後冒出幾點很顯著的八十年代大台電動的電子喇叭音效,像是《小精靈(Pacman)》裡面被鬼抓到時的聲音,至於為什麼不是把鬼吃掉?也很簡單:邪魔壞蛋都要先猖獗一下,再讓天兵天將來收拾嘛。
後面出來的人聲反覆吟誦「三牲獻藝」,變聲後聽起來也有點童音,就像是《小精靈》那個時代的電玩主角會有的腔調。至於為什麼廟會音樂要和電玩音效放在一起?也很好理解:廟口通常都有市集,市集當然要擺一些大台電動機台,這是 Fish 的童年記憶吧?
電子遊戲的音樂,當然也是電子音樂,雖然當年技術限制,多只能作一些單調的音效,但這單調拿到現在來當素材就正好,聽覺上和歷史文化意義上都好。演到後面,出現了幾種單調的主旋律和順利得分、過關的音效,和似乎象徵著勝利的嗩吶聲交織在一起,果然,正義得勝了。廟會上諸位神將再度威鎮邪魔,廟口邊打電動的小孩也再度過關,美好的傳統世界,美好的我們六、七年級生的童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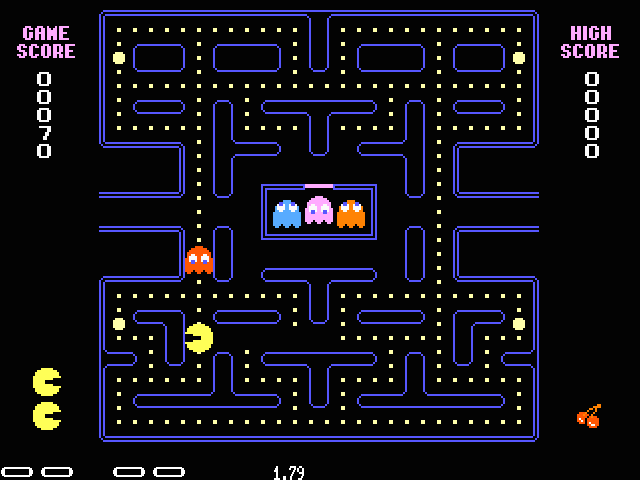
第二首專輯同名曲〈三牲獻藝〉,從聽起來像是路邊收音的吹鼓樂音開展,加入各種音效,也不需費心索解,一聽就能感覺到,這是在描述遶境巡行之時嘈雜、熱鬧、人擠人的街道。廟會音樂,我們雖然每年多少會聽到幾次,但不一定會走出家門去湊熱鬧,這樣是否錯過了什麼呢?像這首〈三牲獻藝〉作出的聲音,不算悅耳;人擠人的街道現場,更談不上舒適,但你就是會感到一種親切,一種人味。
第三首〈獻魚〉,企畫書上寫道:「……完全跳脫所有框架,僅以極簡鋼琴演奏,將台灣最具代表性的音階曲式徹底轉化,企圖突破所有人對於傳統/電子音樂的框架。」翻譯一下:這是一首長達九分鐘的鋼琴獨奏曲,內容就是把廟會樂曲的嗩吶音階改用鋼琴彈出來,
啊,我們從小聽的那些熱鬧繁雜、也不知到底在講些什麼的曲子,如果將之簡化到只剩主旋律,大概就是這樣。至於這聽起來像什麼?好像有一點數學的趣味,而古代的音樂、數學、政治、信仰,向來是很有關係的,那它可以拿來作什麼呢?似乎可作復古的電玩音樂,像是《青蛙過街》那種和神明遶境在概念上有點類似的。遊戲界同仁不妨試試!
和曲名的對應也不難解:《周易》「中孚」卦辭「豚魚吉」,小豬和魚,在傳統上是比較不貴重的祭品,祭品不貴重然而心誠,就是吉祥的。現代講的三牲,是不嚴格規定的三種肉類,不必大手筆地用全豬、全牛、全羊,只要一塊豬肉、一隻雞、一條魚,也就夠體面了。其中,魚相對於禽畜,感覺和烹飪方法又比較清淡一點,所以這裡用鋼琴來表現,也是很合理的。
第一首〈威鎮邪魔〉寫人的記憶,電玩與廟會的互文;第二首〈三牲獻藝〉白描現場街景;第三首〈獻魚〉以簡化的蹊徑來探討廟會音樂的本質。Fish 從不同方面做出了他對本題的三道菜,樂風雖前衛,思路卻是相當正宗,易於理解,也對勁。如果要拿「傳統的翻新與轉化」這個新八股來寫命題作文,Fish 這三首是最好寫的。但那有什麼意思呢?不如來討論看看能不能從這音樂的概念出發,跨界合作寫幾套廟會遊戲,大家就可以把神明存在手機裡隨時隨地滑幾下來供奉了。

空方-柯智豪
柯智豪的收尾之作,有歌詞,應該是我的研究專業最能派上用場的,可是我又聽了幾遍,竟發現他的音樂比前兩位都難。「海方」的 fish,表現的是當代的人文;「陸方」的音速死馬,表現的是他一個跨次元智慧生命的所見;而「空方」柯智豪試圖表現的,是民俗文學與酬神戲曲的空域。
〈浣衣溪畔見綠苔〉和〈此後我心無掛慮〉都是七言詩,這體裁或者叫「竹枝詞」,或者叫「七字仔」,是通俗的、較口語化的,你在文人的寫的近體詩裡,很難看見「浮水搖漾實可愛」這樣直露,或「轉眼又過三十年」這麼尋常的句子。對象、主題不同,自然該作不同的語言風格。
〈浣衣溪畔見綠苔〉原型的故事:漢初,今湖南郴州的一個村裡,有一位潘姑娘在溪邊浣衣,有所感應而成孕,十月後生了一子,此子自幼有各種神異,後來由仙師賜名蘇耽,成道飛升後也遺澤家鄉,救了一場瘟疫,鄉人感念而祀奉之,名為蘇仙。這種神仙故事在歷史上很多,特別是道教系統的小說戲曲,然而,這首歌裡是怎麼表現的?
一開始是鋼琴,似乎表現著靜謐的溪邊,然後又加了些鑼鼓,似乎是表現廟會舞台上,演著這齣戲的人;再之後,男聲合唱出來了,是很中規中矩的吟唱,感情是虔敬的,而不是神入那位戲台上的正旦。大概這就是神明戲和文明戲的差別──唱詞主要是渲染這種虔敬的氛圍,維繫傳統的群性,而不在乎個性的發展與突破。此曲很短,不到一分半,歌詞唱完一遍,音樂漸漸轉向空靈,就接下一首〈小法迎神〉了。
企劃書裡提示了「台灣新浪潮電影場景」,敢是《悲情城市》裡湊巧拍到的送葬行列那樣嗎?那要講,似乎也就只能沿著那道思路,說這是音樂人對這種場景、文化的體認與回饋。但如果只這樣講,那也等於沒講。尋思許久,也只能用最近想出來的一個理論來說:「群性、個性、超越性」,這是支撐一個作品、藝術家,乃至一個文明的三角,

如前面的〈浣衣溪畔見綠苔〉歌裡,女主角的「個性」隱而不顯,由虔敬的男聲合唱來顯現為一種「群性」;接著引向空靈的音樂,則是引向一種「超越性」,道家的,混同的,天人合一的,東方文明的超越性。西方文明的超越性又是怎樣呢?源自西方的電子音樂,內稟有多少西式的超越性呢?我們這種東方式的超越性表現,又可以與之形成什麼對話呢?柯智豪這四首歌曲與樂曲就是在做這個經典的習題:調和個性、群性與超越性,調出他所感受到的台灣民俗信仰代代相傳的調子。
〈此後我心無掛慮〉長達將近六分鐘,歌詞唱兩遍,第一遍和第二遍之間接一長段很玄的音樂,第二遍之後也有一段很玄的吟唱。歌詞講的可能是蘇仙飛升以後,蘇母憑他留下來的法寶(可以變出足以維生的日用品)獨自安居,活到一百多歲無疾而終,所以「轉眼又過三十年」唱兩遍也是合理的,一遍可能不夠,三遍必定太多了。會在意這種細節是受 Zonble 樂評〈唱詞中的動作〉 的影響。
〈此後我心無掛慮〉的合唱和之前的〈浣衣溪畔見綠苔〉是同一批人,同樣的風格,然而有次第,一次比一次更……「圓滿」一些,這是我想到最接近的形容詞,或者該用道教的「混元」?不論如何,柯智豪是在處理一種生命,一種看待生命的態度,傳統民俗與信仰裡的生命觀。
蘇母(其實應該叫潘姑娘)未婚成孕,原是不光彩的,但所生的兒子成了神仙,還救濟了鄉民,這就可以讓她「此後我心無掛慮」了。蘇仙飛升後,蘇母一沒有嫁人,二沒有拿他留下來的法寶變東西來賺錢,三也不開神壇不幫親戚作土豪,情欲、財欲、權欲皆無,就那麼平淡自在一個人過完下半輩子,這反映了古人的道德觀,對有道之人及其親屬的期望,這是好還是不好?
這一過程是否也算一種「吃人禮教」?然而扯這個是學者和小說家的作業,不是音樂人柯智豪的功課;柯智豪做的,只是呈現這樣一種虔敬的期望、清淨的嚮往,這樣一種群性與超越性。個性也是有的,就在他這四首曲子的編排與貫串裡,但是很不明顯,融化得不見痕跡。但我想他大概也就是這樣一個善於配樂、甘於配合的人吧?這樣的性格,也的確最適合來為這張專輯收尾了。

電子音樂可以提供什麼傳統神道或文化的滋養?
《三牲獻藝》可以為我們再建什麼神道?亦或是與傳統文化有什麼匯流的可能?我認為台灣民間唯一能與資本、政黨相匹敵的力量,便是「宗教與民俗」,而民俗的潛力可能還比正式宗教更大。但因為中華民國在建國思想與憲制上都排除了國家神道的可能,所以民俗信仰就上不去;受西式教育的知識份子,也再不能像王朝時代的士大夫那樣,以其精神氣象,引領民間神道,一同統率天下文明。
那麼我們還有什麼人,可以做出更新神道的功業?直接講答案:「音樂人」,能直接使大眾聽見的音樂人。幾十年來,都有音樂人在做這等事,《三牲獻藝》也不是第一張探討這種可能的專輯。前此,黃克林、謝宇威、交工、閃靈、董事長,還有那些野生的「電音三太子」都做過, 只是《三牲獻藝》第一次如此密集地運用不拘一格的音樂,來描繪這些廟會、信仰與歷史的精神氣象,其多樣性與整合性,超越了以往那些只有一兩首的、只沾到邊的、只顧感官的,或者太過簡單武斷的。
為什麼我在乎這個「神道」呢?
古語說「神道設教」,信仰和政治向來密切相關,世界各國,歷朝歷代,多少都要用信仰來鞏固政體,一方面借助神道,一方面也防範神權坐大。中國歷來的辦法,是用士大夫主導的「國家神道」(這是我的命名,或許還可修改),壓制巫性,削弱神性,突出聖人崇拜的儒家思想,去統攝、收編各地的民間神道,一起繁衍擴張,同化異族。
擴張到近代的台灣,原本也該是這樣的模式:移民把故鄉的神衹帶過來,官府則主持統治階級所繫的孔廟,用思想和現實的雙重威權治理民間;可是,出問題了──天高皇帝遠,民風剽悍,官威低落,官府頂多能聯絡仕紳,和幾個頭面人物打交道,對刁民就沒辦法了。其結果,就是國家神道的影響力,沒能像民間神道那樣深深紮根,雖然民間也尊重讀書人,各地宮廟也教忠教孝,但其格局,就不免限於鄉里,止於「齊家」就好,而不去培養「治國平天下」的抱負。
然後清朝把台灣輸給日本了,日本是君權、神權一體的神國,也帶了他的國家神道來蓋神社,但五十年的時間並不足以解決水土不服的問題,近代化的教育體制與政治思想,也已和傳統的神道有各種矛盾,不像一千多年前可以來個「諏訪大戰:土著神話 vs. 中央神話」 ,打完慢慢磨合。
過去我們讀台灣史,讀過很多台籍知識份子對日本的各種糾結,但好像很少看到庶民層面,日式神道對漢人民俗信仰的影響。雖然你也可以說,這是因為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後把日本神社拆了,但無形的影響應該不那麼容易洗掉抹去。再者,日本神系和華夏神系,神道教與漢人的道教畢竟不是一個系統的,而現世的政治上又是殖民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,或許也因此難以發展出多少相容性了吧。
同樣經受西潮衝擊,1945 年後接管台灣的中華民國,其國家神道又是另一幅光景──幾乎完全摒棄了。現代化的概念,嚮往西化的知識份子,將一切神道斥為迷信,也不去想更新國家神道與民間神道的可能,只想用科學與人文藝術(如朱光潛的「以美學代替宗教」)來取代。民國初年還有一些沿襲著老規矩的人和做法,但是沒有在國家層面上定制下來。國家保留的祀典,只祭人鬼,包括孔子,不祭天神地祇。
這樣,地祇完全由民間來祭,政府首長只是拿香跟著拜,無能主導,亦無法(法律)主導。國民黨在俗世的統治雖比清朝高效,但在信仰的世界,便完全無法作主了,每年祭孔典禮,也難看得要命,儀式、樂舞,無不死氣沉沉,虛應故事,脫離現實。唯一勝過日本的,也只在「中華道統」這個共同身份上;宮廟於是在意識形態上和國民黨可無衝突,現實中更可以一起發財,無須作對。
在這種生態下,國家不能貫通民間神道,又逐漸民主化,那就是掌握了地方宮廟的角頭,經固樁綁樁,逐漸侵奪而架空了國家,現狀就是這樣:他們可以不買兩黨的帳,兩黨卻不能不買他們的帳。然而能在地方政治裡勝出的政客,大概也很難有什麼文明的大格局;受現代教育,讀西方學問的知識份子,對此更無能置喙,甚至很多人是下意識地根本反對神道設教,排斥神道所能產生的作用 ,遑論在民俗神道和現代政制的基礎上,重新給台灣建立一種適合這個民主時代的神道,更遑論由此展望與世界文明的對話,以及全人類的未來了。

那麼,《三牲獻藝》可以給我們揭示某種新的未來嗎?我的感想是不能。他們沒有那麼偉大。但有幾個音樂家能這麼偉大?不要太奢求了。
然而「藝術在使人看見」 ,就「描繪所見」這一點而言,這三位誠實又詭異的音樂人,已經做得極好了。我不懂電音,民俗我也只學過一些書上的知識,體驗不多,但這張《三牲獻藝》我都聽懂了,我完全聽得見他們想講什麼,雖然對音速死馬的作品還沒能用這個次元的語言來描述我的感想,但這才更可貴。不是嗎?
或許是音速死馬那種更講究靈覺與異感的,或許是柯智豪那種對生命終極關懷的回歸,或許還是黃凱宇的思路比較可行:做遊戲吧!打電動打電動。我們遊戲界的同仁,也真的應該想辦法和地方宮廟結合;有誰要做,別忘了叫上我。
最後,三個月前我看到的「益」卦與「咸」卦,何解?也很簡單:風雷激盪,令人類自覺精進,文明得以增益:「風雷,益,君子以見善則遷,有過則改。」「咸」則是「感」的意思,用性交來打比方,說出「君子以虛受人」的道理。聽過《三牲獻藝》整張專輯,確實,他們讓異種的音樂、文化在自己的身心靈上相交,之後作出來的,也不是斬釘截鐵的政見,而是開放的光景。
這或許是當代臺灣可以具備的全新神道,庶民文化的重新匯流與集結。
Photo Source
吹音樂:渾身崑崙!混種電音再臨 三牲獻藝找上太子爺| https://blow.streetvoice.com/15019
Indievox|https://www.indievox.com/samsenghiange









